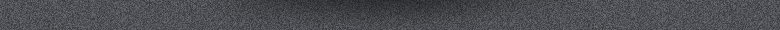ghdhair100
ORANGE EKSTRAKLASA
Dołączył: 15 Gru 2010
Posty: 2005
Przeczytał: 0 tematów
Ostrzeżeń: 0/5
Skąd: England
|
 Wysłany: Pią 3:43, 04 Mar 2011 Wysłany: Pią 3:43, 04 Mar 2011 |
|
|
人物素描(续) - 王明洋的博客 - 敏思博客
人物素描(续) 王明洋 舅妈 我的一位远房舅妈,不到五十便离开人世。我一致认为她是被活活气死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虽说已进入文革末尾,但正如人的“回光返照”,闹腾劲依旧颇凶。这位舅妈的丈夫,亦即我的舅舅是刑满释放分子,村里大凡开什么会,都要被不点名地敲打一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村干部的讲话也可能出于习惯性思维,“例行公事”,毕竟还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舅妈倒时常为此较真儿,不依不饶,众目睽睽之下,“蓦”地站起来,冲村干部喊:“要批就批我吧!”那时,遇着类似“大是大非”问题,即便是亲生父母,为此声明划清界线的,大有人在。舅妈可好,竟敢“逆历史潮流而动”,难免要被人视为“螳臂挡车,自不量力”了。好在村干部“宽宏大量”,对她与政府的“公开挑衅”不予理睬。不过在以后的大会上,对舅舅依旧是不点名地进行敲打,舅妈依旧是当众站起来表示强烈抗议。因为是“例行公事”,村干部不可能动起“真正的阶级感情”,对于舅妈的“无理取闹”,完全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舅妈可是动了真情的,气大伤身。较量的结果,舅妈注定会一败涂地。 如果说,皇上的工,慢慢蹭,开大会,村干部不会动真气,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亦是肉体之身的村干部就不会那么超凡脱俗了。在这种场合,舅妈与村干部发生冲突,定是以卵击石。这对舅妈的打击愈发沉重。一天早起,听见大街上有人吵架,便出来看热闹。舅妈的邻居,即一位村干部盖房划宅基地时,舅妈说他侵犯了她的宅界。双方为此发生争执。这次争执,村干部可是动了真气,当众抽了舅妈一记耳光。争执的结果不得而知,但那记耳光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挨打的舅妈,瞪着一双大眼,流露出愤怒惊讶屈辱无奈和绝望,终于忍不住流下两行泪水。 给予舅妈致命打击的,我想应是她大儿子即我表哥的过早离世。舅妈的几个孩子中,数表哥懂事,在村里口碑挺好,这对命途多舛的舅妈是最大的或许是唯一的安慰。当时地区正修建当地著名的大水库。农村调集大量民工,分期分批参加水库建设。表哥二十岁那年出外当民工。那时出外当民工,可不像现在的进城打工挣钱。大凡大的工程,“全民皆兵”,搞人海战术。虽苦点累点,起码能吃饱肚子,还不时改善生活。参加完朱庄水库大会战的民工一回村儿里,这个胖了,那个瘦了,竟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胖的居多。若是哪个瘦了,大抵是在家娇生惯养,丝毫引不起人们的同情。当民工不长膘,意味着既不能吃又不能干。表哥属于既能吃又能干之列。在一次改善生活中可能吃肉太多吃着了,竟一病不起,最后死在工地上。那天,我参加了表哥的葬礼。临下葬时,舅妈让人打开棺材盖,想最后看一眼儿子。只见表哥穿一身藏蓝色衣服,外面套一件藏蓝色半大衣,戴一顶藏蓝色帽子。脸腊黄。几乎哭干泪水的舅妈往表哥的大衣兜儿里塞一副崭新的扑克,然后磨转身默默地站在一旁。主持葬礼的立即命令手下人钉死棺材盖。一边“砰砰”地钉着,主持人一边呼喊着表哥的名字:“某某看钉!某某看钉!” 没多久,舅妈便患癌症去世了。舅妈临死时,瘦得两只眼睛大得吓人。母亲经常对着我们数落舅妈:“她吃亏就吃在那张嘴上了!” 舅舅将舅妈年轻时的一张黑白照片,镶在镜框里,一直在墙壁上挂着,透着压抑悲伤和沉甸甸的思念。舅舅至今没有续弦。 大大娘的偏方 现在,不知是工作忙,还是感情上的“日疏日远”,家乡来了人,不管人家有事相求,抑或专程探望,总觉得是一种负担,总是隐隐地有些不快。与小时候,简直判若两人。 刚从老家回到父母身边,天天盼老家能够来人,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平时,我视家庭为牢笼。倘老家来了人,又恋家恋得厉害。不想上学,在教室里,失魂落魄,度日如年。大大娘来得最勤,每次来都要海(小住)几日。母亲对大大娘好象颇有成见,大大娘高高大大,肥肥胖胖,母亲对着我们称之为“母老虎”。后来方知,大大伯死得早,大大娘改嫁了。改嫁后,还时常来往,也难怪,自己的儿子儿媳都在老家,绿叶成荫子满枝。大大娘的到来,给我带来不少乐趣,老人家颇健谈,经常陪我们聊天说话解闷儿。我对刚刚离开的老家最关心也最感兴趣,魂牵梦萦啊,毕竟在那里生活了七八年。大大娘即老家的化身,看到老人家,就等于回老家周游了一遭儿。大冬天,小手背冻得粗糙皴裂,时常渗着血,疼痛难忍。大大娘给我推荐了一个偏方。她拉我到洋槐树下拣一包干巴的麻雀屎,再打半盆滚烫的水。她先是用自己的手蜻蜓点水般沾一些开水撒在我手背上,开始烫得生疼生疼,直吸凉气。渐渐地由生疼而痒痒而麻木,竟嫌撒开水不过瘾,干脆将一双手泡入依旧滚烫的水里,顿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通体舒坦。正在如痴如醉地泡着,大大娘毫不客气终止了我的享受,她往我手心撒几粒麻雀屎,权当是“香皂”,叫我手心手背不停地搓呀搓,搓毕,用开水洗净。睡一晚上,第二天,那小手竟脱胎换骨似的,红润而有光泽。我时常想,手模特的手所以能保养得那么好,大抵离不开麻雀屎的滋润吧?即便有特效的护肤霜,想必都含有麻雀屎的成份,甚至主要成份也未可知。 车间主任 刚参加工作时,在某煤矿车间当铸工。我们的车间主任姓严,人如其名,活泼不足,严肃有余。别人还钱时,大抵都要推推搡搡,拉拉扯扯,极力做客气状。这在我国,好象已是约定俗成的事。但严主任不,每每是面无表情地接过来,毫不客气装入口袋。 我们的车间副主任姓什么,记不甚清了。小名乱小,抗日战争生的。头发自然卷,国子型黑脸膛,方方正正。他经常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逢人便说,这几日老打嗝,不是好现象。他怀疑自己的肚子里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严主任每每不以为然地笑笑:“我看是心病。” 我调走没几年,听说严主任患癌症不在了。十几年后,陪父亲到医院看病,与我们的车间副主任碰个正着。他那自然卷的头发已有些花白。他依旧捂着肚子,愁眉苦脸,冲我直摇头:还是老打嗝。 脏舅 脏舅并非舅脏。他的小名叫老脏。 脏舅从小爱取笑人。 “你看久长有没有文化,说话还爱用个词儿,‘非同小可’,还‘非同小可’!”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出去给人家撞车了,回来和我们说当时的情况,一脸的不屑:“撞就撞了吧,口气还不小,问我‘你知不知上下道?’自以为老粗不细儿的,还‘上下道’!” 后来也曾遇到过类似脏舅这样爱挑别人毛病的人,他们讲得每每是津津有味,维妙维肖。又如漫画家,虽有些夸张,但十分有趣。我敬佩他们的观察能力,却不欣赏他们的处世哲学。他们用特别的目光去看特别的人,但并非把“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而是把“特别的笑献给特别的你”。这样的人一旦当了领导,定是武大郎卖炊饼,你休想高他一寸。如果他与当年的陈胜吴广在一起,人家说“王候将相,宁有种乎”?他还不把人笑话死!定责人家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断不会说“苟富贵勿相忘”。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被他“消灭”于萌芽状态,也未可知。幸亏脏舅现在还是一介普通农民。国家幸甚? 不过,脏舅天生是个乐天派。可能是一介平民,没有进喜,没有退忧,又喜欢拿人取乐,使这种乐天派的性格“锦上添花”或“变本加厉”。“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却勿须“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这对他本人未必不是一件幸事。我以为这亦是一种天才。
Many years ago there lived an Emperor who was so exceedingly fond of fine new clothes that he spent vast sums of money on dress. To him clothes mean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He took no interes
related links:
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具备的。
Post został pochwalony 0 razy
|
|